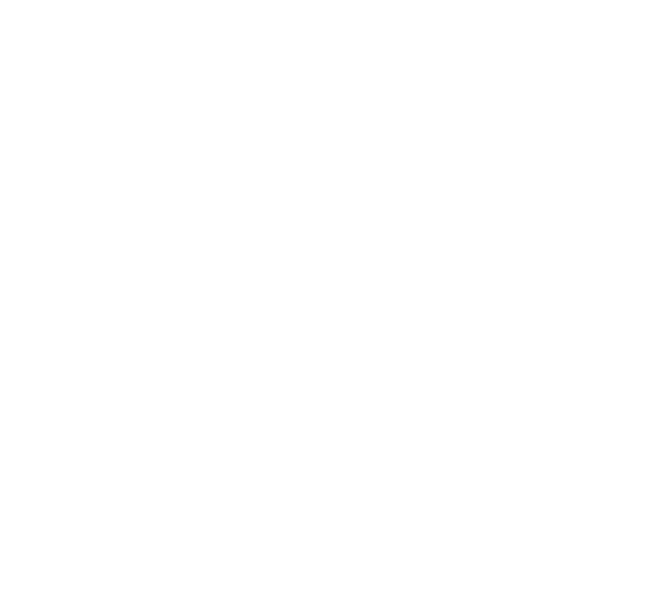敦煌文书案例中的法律智慧
发布日期:2023-11-08 11:20 信息来源:机关党委 访问量:? 字体 :[ 大 ][ 中 ][ 小 ]
□ 韩伟 闫强乐
敦煌文书的再现是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重大发现之一。与安阳殷墟甲骨、居延汉晋简策、明清大库档案相较,敦煌文书具有形式多样、数量庞大、跨越时间长、使用语言多、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等特点,具有极高的文物珍藏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敦煌文书中大量的司法案例为我们进一步地认知中国古代的司法智慧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案情简介:郭泰、李膺,同船共济,但遭风浪,遂被覆舟。共得一桡,且浮且竞。膺为力弱,泰乃力强,推膺取桡,遂蒙至岸。膺失桡势,因而致殂,其妻阿宋,喧讼公庭,云其夫亡,乃由郭泰。泰供推膺取桡是实。郭泰、李膺,同为利涉,扬帆鼓枻,庶免倾危。岂谓巨浪惊天,奔涛浴日,遂乃遇斯舟覆,共被漂沦。同得一桡,俱望济己。且浮且竞,皆为性命之忧,一弱一强,俄致死生之隔。阿宋夫妻义重,伉俪情深,悴彼沉魂,随逝水而长往,痛兹沦魄,仰同穴而无期。遂乃喧诉公庭,心仇郭泰。披寻状迹,清浊自分。狱贵平反,无容滥罚。且膺死元由落水,落水本为覆舟,覆舟自是天灾,溺死岂伊人之咎。各有竞桡之意,俱无相让之心,推膺苟在取桡,被溺不因推死,俱缘身命,咸是不轻。辄欲科辜,恐伤猛浪,宋无反坐,泰亦无辜,并各下知,勿令喧扰。
《唐律疏议》中关于杀人命案,规定有故杀、斗杀、谋杀、戏杀、过失杀等不同的形式,被后人总结为著名的唐代“七杀”理论。“七杀”理论基于司法实践的经验,涵盖了“命案”犯罪的主客观各个方面,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应用。结合本案例,不难发现,造成李膺死亡的(且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郭泰在整个事件中确实并无杀人之心,他只不过是在“舟覆落水”这一危急时刻,与李膺共争救命之物——桡,李膺力弱,未能争得桡,从而导致了死亡的不幸结果。如果暂时排除主观动机和客观因素不谈,在该事件中,毕竟造成了死亡的结果,所以是可以归入“命案”的,既是命案,就可以首先使用唐代刑法中的“七杀”理论进行分析。其一,唐律中对于“谋杀”是这样规定的:“谋杀人者,谓二人以上;若事已彰露,欲杀不虚,虽独一人,亦同二人谋法。”即唐代的“谋杀”是要求具有“二人以上”“对谋”这样一些要素,该案仅有郭泰一人,非“二人以上”,也没有“对谋”的情节,所以“谋杀”是最先被排除掉的。其二,关于“劫杀”,唐律也有明确的规定,“若因窃囚之故而杀伤人者,即从劫囚之法科罪”,就是指因劫夺囚犯而杀人,在所引案例中,也看不出李膺是“有罪之人”,也不是发生在劫夺囚犯的情况下,所以也不是劫杀。其三,唐律中的“戏杀”是指“以力共戏,因而杀伤人”,李膺、郭泰同舟,落水后各自出于本能争抢一桡,均是出于理性的行为,而绝非“嬉戏”之举,所以也不能划入“戏杀”的范畴。其四,唐律中的“误杀”是指有杀人意思,但是现实中被杀的人并非所想要杀死的人,即错置了杀人对象,对照本案,郭泰显然也不能称为“误杀”。其五,“过失杀”在唐律中是指“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即因过失而杀人,郭泰显然不会不知道推李膺入水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行为不具有过失性,所以也不是“过失杀”。排除了上述“五杀”,那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故杀”,要么是“斗杀”。唐律中关于“故杀”如此规定:“以刃及故杀者,谓斗而用刃,即有害心,及非因斗争,无事而杀,是名‘故杀’。”强调的是争斗中即有害人之心;而对“斗杀”是如此解释的:“斗殴者,元无杀心,因相斗殴而杀人者,绞。”不强调有“杀心”,杀人只是斗殴的一种“意外”结果。如果仅仅以上述条文来看,郭泰的行为似乎更符合“斗杀”,两人争斗,而导致一人死亡,郭泰“元无杀心”,因相斗而致人死亡,理应属于“斗杀”。但是,仔细分析,“斗杀”又有不合,因“斗杀”的前提是要两人相斗,即有斗殴之行为,郭泰、李膺两人在生死关头共争一桡,是出于本性,并非有心而斗,所以定为“斗杀”仍然欠妥。这样分析下去,似乎“七杀”皆与本案不合,郭泰应属无罪。
但是,在《唐律疏议》中还有一类条款不能不提,那就是“以……论,准……论”的准用型条款,翻检律文,可以发现仅是“故杀”,就有好多准用型条文。《唐律疏议》之《贼盗律》中,“以物置人耳、鼻及孔窍”及“故屏去人服用、饮食之物”而准用故杀条就与本案有诸多契合之处。该条疏议曰:“若履危险,临水岸,故相恐迫,使人坠陷而致死伤者,依故杀伤法。”该条之罪为结果犯,一般没有杀人故意,“至有杀心,即以谋杀科之”。郭泰等人“被覆舟。共得一桡,且浮且竞”,可谓是“履危险”,“膺为力弱,泰乃力强,推膺取桡”,“推”当为一种逼迫,称之为“故相恐迫”也不为过,所以,该条疏议的表述最为接近本案。
综合以上分析,对于郭泰的行为,根据《唐律疏议》之规定,依照“故屏去人服用、饮食之物”条,准作“故杀”论,较为妥当。
(文章节选自韩伟、闫强乐《中华优秀法治文化十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吴亚洁)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冀公网安备13010402001751号
冀公网安备1301040200175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