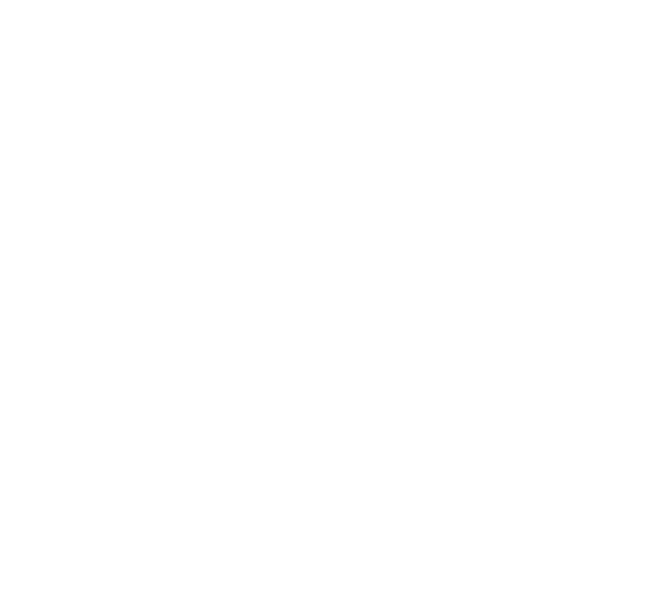看河人
发布日期:2024-12-06 15:54 信息来源:科技与宣传教育处 访问量:? 字体 :[ 大 ][ 中 ][ 小 ]
其实我只是想通过一个人讲述一条河的故事。——题记
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和同龄的其他孩子没什么两样。
村子在长城脚下,不远处就是一条河,人们叫它潮河。潮河的水如果不赶上发洪水还是很清的,可以看见里面游来游去的鱼儿,有鲤鱼、鲫鱼等。他是自小在潮河里泡大的,少不了常去河里抓鱼,那时候的人不大钓鱼,用一个竹簸箕朝河里只那么一撮,端出来便是满满的活蹦乱跳,用柳条串成串晾干,过过油,甭提多好吃了。吃不了的就找根竿子挂在公路边上,过往的司机一招手,鱼递进去,钱递出来,家里的零花就有着落了。
当然,这大多是大人们操心的事儿。像他这么大的孩子除了帮忙抓抓鱼,更多的是在河里寻找自己的乐子。
开春的时候,夜里躺在炕上会听见“咔嚓”“咔嚓”的响声,潮河水化冰了。过不了多久,开裂的冰块开始缓缓移动,两岸草青树绿,护佑着一河清水向远方流去。
河面上来了许多鸟,各种各样,不知从哪飞来的,叫不上名字。他只知道一种叫“野鸭子”的,杂灰色,草窠里做窝,成群结队地凫在水面上。其他小伙伴们都喜欢去草丛里撵鸭子,鸭子很少撵上,窝里的鸟蛋却遭了殃。可他不喜欢,他常常一个人坐在岸边高处呆看着这潮河上的精灵,一坐就忘记了时间。久而久之他可以分辨出雌雄来,公鸭绿脑袋,母鸭灰脑袋。还有一种长腿的“河溜子”,不善飞善跑,一般人根本撵不上。有一天他发现一只“河溜子”歪倒在草窝里,走近一看原来是腿折了。他把它带回家,用布条把腿缠上,拿来棒子面饽饽碾碎了塞进它的嘴里,可它根本不吃。他又去河里捞来小鱼喂也不吃,没过两天这只“河溜子”就咽气了。他非常伤心,决定把它葬在潮河边上,他觉得它应该属于那里……
农村的夏天炎热而漫长。孩子们喜欢背着爹妈整日地泡在河水里,嬉闹的声音即使到了微冷的秋天还荡漾在两岸晃动的杨树梢上,惊走穿行于繁枝密叶间的鸟儿,把美妙的禽音丢给这群赤裸奔跑的孩子们。他和小伙伴们站在岸边的高处,甩掉衣服,绷直身体,紧闭双眼,“扑通、扑通”扎进水中,然后从河底搬起一块石头站起来高高举过头顶,像举起一面面胜利的旗帜。草丛中有的是蚂蚱,一只,两只,串在草梗上,活蹦乱跳的。这是鸡的美食,鸡吃得好,蛋就多,卖的钱就多……
1976年夏天,潮河发了一场大水,浑浊的水浪将岸边掏空,一棵棵十来米高的杨树顺水漂走,但却保全了不远处的村子。洪水过后的入秋时节,村里男女老少一齐出动,补栽了杨树,没过两三年杨树又连成片了。随着杨树一天天长粗长高,他和他的伙伴们也一天天长大了。不过,这些年来他有一个习惯一直没变,就是一有空就喜欢坐在潮河边的高处,长久地凝视着流淌不停的河水。他喜欢这样,说不出为什么。
二十几岁的他和其他伙伴们一样娶了媳妇成了家。村子人口多了,房子盖得也离河边越来越近。当时沿河上下的村子都鼓动种水稻,人们开稻池,挖水渠引潮河水灌溉,种出的稻米晶莹剔透,很有筋道。提起潮河川的大米远近闻名,人人都竖大拇指。从此以后,人们告别了上顿棒子面、下顿棒子粥的日子。不过他慢慢发现这些年老天爷似乎不咋下大雨了,再加上稻池灌溉,潮河的水在渐渐变浅变细。想当年即使到了冬天潮河的水也是不会完全封冻的,他和伙伴们滑冰都要拣靠近河边的地方,河中间是万万不敢去的。哪怕遇到寒冷的年份河的表面完全结冰了,你趴在冰上还可以听到下面汩汩的流水声……潮河,是一条四季流淌永不停止的母亲河,滋养了上下游四里八乡的土地和人口,见证着沧桑的岁月变迁。可如今……他有时手里端着白米饭,感觉没有原来那么香了。
90年代末期的时候,潮河边上陆续建起了一些工厂。建工厂需要大量的沙子,许多人便去潮河里筛沙子,据说很挣钱,比种庄稼强多了。特别是到了枯水期,河床上就会出现了许多挖沙的人,甚至有大型的采砂机器在作业。人们像一个个执着而辛苦的淘金者,努力地淘着自己的生活。他没有加入挖沙的人群,他不想这样做,只是依旧有空的时候去河边转转,然后坐在岸边的高地上凝望着这条已经有点变了模样的河流。河里的鱼是越来越少了,野鸭子也越来越少了,岸边的杨树还在,长得很高大,只是变得稀疏了,河里窄细的水流似乎告诉人们再也不必担心有什么大洪水了。村里每当有老人过世,人们就伐一两棵大杨树做棺材,村里的干部们也都默许,让这种做法渐渐成了一种风气。
有一天,他在河边干活,一群光屁股的孩子欢叫着从身边跑过,扑腾腾跳进了河里。看着这群无忧无虑的孩子们他不禁想起了自己小的时候,也是这么无忧无虑,也是这么……突然,远处传来哭救的声音,他紧步跑过去,衣服也来不及脱就跳进了水里。可是已经晚了,一个孩子游进了挖沙的暗坑里……他把孩子抱到岸上时已经没气了……孩子的父亲领着几个人到河边砍下一棵杨树做成棺材,埋葬了这个十几岁的孩子,然后继续挖着他们的沙子。
这之后他很少去河边溜达了,实在坐不住就到村后的山上,远远地张望着这条千疮百孔的河流,本就不太爱说话的他变得越发沉默寡言了。
2000年后的一段时期都流行卖地,村里的不少土地也被卖给了企业,盖了工厂。地越来越少了,他便去了一个厂子打工。厂子离村子不太远,生产什么东西说不准,听说要出口的,有人说人家外国人不产这个,污染大。他第一天进到厂里就闻到一种怪怪的味道,让人不舒服。工人倒不少,有百十来号人,都戴着口罩干活。厂里不时有人辞职,也不断有新工人进来。他在这个工厂干了大概三四个月的光景,实在是受不了那种味道,最后还是辞职回家了。
回家待了一阵子后,他打算到潮河边走走,已经有一阵子没去了。虽然心里有些准备,但眼前的样子还是让他感到很意外。水越来越少,有的地方已经裸露出了石头,像啃噬后剩下的动物森森的骨架。大大小小的沙坑遍布河滩,有的旱滩被村民开垦成了庄稼地,这一块那一块地圈起来,岸边倾倒着一堆堆的生活和建筑垃圾,许多各色的塑料袋泡在水里。那些杨树还在,只是更加稀疏,无言地凝视着这条伤痕累累的河流……他沿着河边向前走,发现有一根水泥管子从边坝里伸向河道,管口流着浑浊恶臭的脏水。他继续往前走,发现走不上一里远竟然就有十多根这样流着臭水的管子,其中有一根就是他打工的那家工厂的……他没法再看下去,心情极其沉重地离开了。
他终于真真正正地大病了一场,一个多月才缓过劲来。此后他变得爱看电视,而且专拣央视新闻和本县的节目看。从新闻报道中他渐渐感到国家对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了。终于有一天,村里挖沙的人不再挖沙了,河道里出现了几台推土机,轰隆隆地响了好几天后,沙坑全部被填平了,岸边的垃圾也被陆续清走,所有的排污管子都不见了,一些工厂也接二连三地搬走了。河道上修了几道透水坝,这样水面宽敞了许多,也渐渐清澈,在阳光的照射下像一面亮晶晶的大镜子。看着这些变化,他甭提有多高兴了,每天都要去潮河边上走一走,瞧一瞧。
潮河的环境越来越好,景色越来越美。两岸进行了绿化,栽植了许多杨柳和果树,修建了廊桥,种下了荷花。景致美了,来的人也就多了。有的人家办起了农家院,主打菜就是潮河里的鱼,这样收入增加了,日子也就越来越好了。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最近又听说要建什么国家湿地公园,看来以后的日子还真是很值得期待呢。
他最近心情很好,每天都去潮河边走走,感觉是越来越有看头了。有一天,他发现水面上有几个浮动的小黑点,走近一看,是几只野鸭子,他数了一下,有四只,两只公鸭两只母鸭。四只野鸭子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游来游去,好不自在。他有些激动,像遇到了久违的朋友一样快步走了过去。野鸭子很警惕,看见有人走来,扑棱着翅膀打着旋飞走了。他看着渐渐消失的野鸭子有些懊悔自己的鲁莾,不过他相信,这些精灵肯定还会飞回来的。不久,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人来了,他们说这野鸭子叫绿头鸭,受国家保护呢。他触动很大,决定自己要为这些野鸭子、为这条河做点什么。
终于,他成了一名巡河员,一个看护潮河的人。春天到来的时候,冰面化裂,他要检查和记录具体情况,立警示牌并提醒过往的行人。候鸟飞来时,他要观察和记录鸟的种类和数量,甚至进行投喂并阻止人们惊扰群鸟的生活。夏天到来的时候,他要时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发现和上报雨水对堤坝的影响。特别是暑假期间,学生常来河里洗澡,他也要操心。秋天他要趁着水量的减少检查并修理一些人工景观设施并为入冬做好准备。冬天到了,水面还没有冻严实有些人就走上冻面,他要及时去制止这种危险行为。他已经六十出头,每天挎个水壶早出晚归,没有闲下来的时候,其实这里面的好多工作是他自己加进去的。他觉得自己的“官”不大,但做的事情不简单,意义也不简单。
近几年由于政府重视,投入增加,包括像他这样许许多多的巡河员的付出,潮河的面貌焕然一新。河水清澈,水质优良,水量全年稳定,彻底告别了断流的现象。水里鱼类品种丰富,有鲤、草、鲢、鲫、鲶等多个品种。回归的鸟类也很多,有苍鹭、野鸭、灰鹤、鸳鸯等。有时候几百只野鸭子在潮河上空回旋飞翔,场面蔚为壮观。潮河正以其良好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特别是大量野生鸟类的回归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游玩观赏。
他心心念念的那个水清、物饶、景美的潮河又回来了。
(作者:周海潮 推荐地区:承德)

手机扫描听语音播报
 冀公网安备13010402001751号
冀公网安备13010402001751号